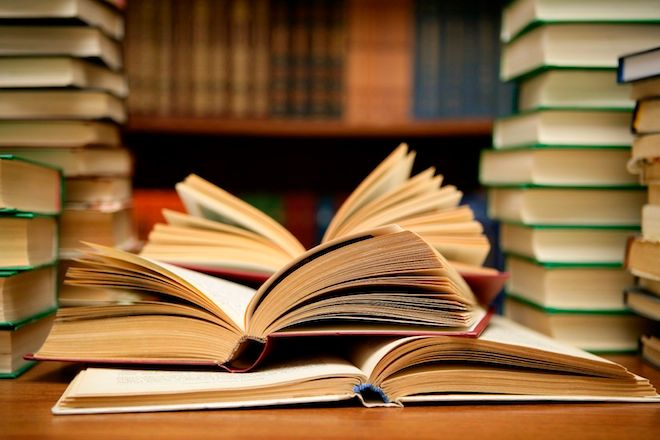武俠小說中的俠骨柔情——以金庸、古龍、梁羽生爲例

梁羽生、金庸、古龍是新派武俠小說最引人注目的“三大家”,其作品創設出英雄美人“攜手走天涯”的詩意江湖,使武俠小說兼備言情小說的特質。頗爲遺憾的是,自從此類小說進入學者的研究視野以來,學術界的研究成果雖不斷湧現,但主要集中在對其創作模式與主題模式的探討方面,偶有對其情感敘事的分析亦是淺嘗輒止。鑑於此,本文結合中國傳統文學創作與評論對“情感”的注重及其積澱與傳承,探討梁羽生、金庸、古龍武俠小說之言情敘事的淵源。
所謂言情敘事,就是以主要人物的情愛故事的發生、發展爲小說基本情節,強調愛情本身的獨特魅力及其對主人公人生的影響力,肯定感性生命的價值。綜觀中國古代長篇武俠小說,其構建故事情節的基本方式是“以武行俠”。例如《水滸傳》《三俠五義》《施公案》等,皆以快意恩仇、行俠仗義爲基本情節,武俠爲公理、道義而生,個人情感則需要剋制,偶有的愛情不過是其俠義生涯的附屬品。從人性的角度看,男女之間兩情相悅,是出於感性生命之本能。特洛爾奇雲:“藝術的現代性因此表現爲對感性的重新發現和此岸感的強化,恢復此岸世界的感性品質的權利。”文藝作品對其渲染本無可厚非。20世紀中期,新派武俠小說崛起。作者以俠客的情感故事爲基本敘事線索,寫俠客們兼備俠骨柔情,在快意恩仇之旅中,追求真愛,營造出英雄美人相知相戀的詩意江湖。這種以情感敘事爲構建故事情節的主要策略是對傳統武俠小說情節模式構建的超越,在以梁羽生、金庸、古龍三大家的作品爲代表的長篇武俠小說中尤爲突出。
在梁羽生的作品中,英雄美人往往在家仇國恨中演繹愛情。柳夢蝶與左含英、婁無畏的愛情糾葛構成《龍虎鬥京華》的主線。《萍蹤俠影錄》中,時代風雲變幻,家族世仇衝突,而張丹楓、雲蕾的戀情是故事發展的基本線索。《白髮魔女傳》以練霓裳與卓一航之間的愛情糾葛構建故事情節。《塞外奇俠傳》中,楊雲聰武功蓋世、縱橫大漠,飛紅巾、納蘭明慧英姿颯爽,其間的複雜愛情構成故事的主線。《女帝奇英傳》是天山下動人心魄的武俠情歌。俊逸瀟灑的李逸與英姿颯爽的武玄霜,知己紅顏,無私摯愛。其浪漫的愛情與無奈的現實衝突,推進故事的發展。此外,《七劍下天山》《遊劍江湖》等,英雄與佳人的愛情,皆是江湖風雲下的純情童話。
金庸以俠客情愛的愛恨纏綿交織爲小說情節發展的內驅力。陳家洛與霍青桐姐妹的柔情蜜意,是《書劍恩仇錄》的故事線索。《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更是書寫俠客愛情之經典。郭靖與黃蓉性格互補,肝膽相照,生死相依,幾經愛情磨難與生命危險的考驗,仍無怨無悔。楊康雖熱衷於富貴榮華,卻對穆念慈一片真心。其愛情充溢着甜蜜、憂傷,結局悽婉而動人。楊過追求真愛、自由,小龍女單純執著,二人不顧傳統倫理、世俗偏見,毅然相愛。《飛狐外傳》中,胡斐把愛情視爲無價之寶,“世上最寶貴之物,乃是兩心相悅的真正情愛,絕非價值連城的寶藏”。《天龍八部》之喬峯與阿朱、段譽與王語嫣、虛竹與西夏公主,其間的愛情磨難共同推進情節發展。可以說,金庸武俠作品寫諸多真情真愛,不勝枚舉。人生的悲歡與愛情的纏綿交織,形成震撼人心的力量。其感染力,較之純情小說,有過之而無不及。饒:道慶指出:“《紅樓夢》和金庸小說的主旨是寫兒女真情、性靈之愛,其癡情的走向是至真至純的摯愛,即情種、情聖這是一種超乎普通人性之上的崇高的愛,是生命的本原,是生命最高價值的體現。”他將其與《紅樓夢》相提並論,讚賞之情溢於言表。
古龍的作品表現的亦是男女俠客之間的真情。《絕代雙驕》《大人物》《蕭十一郎》《多情劍客無情劍》《流星·蝴蝶·劍》《邊城浪子》等等,不僅是刀光劍影的江湖傳奇,更是纏綿悱惻的愛情樂章。江小魚與蘇櫻在江湖血雨中情愫漸生,相依相戀;花無缺與鐵心蘭相互傾慕,攜手同行;楚留香與蘇蓉蓉、李紅袖、宋甜兒相愛相依,共享人生的歡樂;陸小風在刀光劍影生涯中對佳麗流露真情,等等。古龍藉助巧合、奇遇,書寫出愛情的蕩氣迴腸,令瀆者心靈震撼。
任何文學活動,都是與社會心理、情感密切相關的文化現象。新派武俠小說的情感敘事源自中國傳統文學之“情感”影響。中國傳統文學與“情感”之關係可謂源遠流長。《易》率先提出的“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已初步涉及到作品中的情意表達。《荀子》指出“稱情而立交”,重視情感在創作中的作用。《禮記》認爲,“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而“情動於中,故形於聲”。意即創作是真情抒發使然。項羽在軍旅中與虞姬譜寫出“攜手天涯”之浪漫曲,其《垓下歌》發出的“虞兮虞兮奈若何!”是英雄惜美人的真情絕唱。《毛詩序》繼承《禮記》的觀點,將其發展爲“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看到了情感的書寫張力。陸機提出“詩緣情”,將傳情達意視爲文學作品的特徵。傳統文人亦發現,作品的情感書寫是引發接受者共鳴的基本因素。劉勰《文心雕龍》提出“情以物遷;辭以情發”,“觀文者披文以人情”。鍾嶸認爲,情感書寫可“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他們皆肯定作品情感的震撼力。其後,“愛情”逐漸從諸多情感裏突顯出來,成爲大量作品的主旋律。唐詩宋詞大多是吟唱愛情之佳作,其動人力量至今依然。元好問詞雲:“問世間情爲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別苦,就中更有癡兒女。”尤爲動人心扉,被新派武俠小說家屢屢引用,亦是《神鵰俠侶》之“情魔”李莫愁的悽美絕唱。明代文人提出“情本”,強調作品的愛情本位書寫。湯顯祖雲:“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馮夢龍倡導“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僞藥”。在他們看來,故事情節的曲折離奇固然能激發讀者的好奇心,但“情”最能喚起其共鳴。文康提出:“殊不知有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兒女心腸;有了兒女真情,才做得出英雄事業!”其《兒女英雄傳》率先俠情並重,頗具開創意義。町見,從先秦至明清,文學與情感的關係密不可分,特別是諸多作品、理論對愛情的強調,對創作者和接受者都具有深刻的影響力。
丹納指出,文學作品從屬於“在它周圍而趣味和它一致的社會”。社會羣體情感意識的形成源於歷史的積澱。李惠芳指出:“民衆意識的形成,是一個歷史積累的過程。這⋯積層,深厚而複雜:既有古代原始信仰的遺留和傳承,也有後世關於倫理關係、人生態度、善惡是非、生死觀念、價值標準等方面的歷史認同。”傳統文人書寫情感的主張與實踐,經過數千年的積澱與傳承,逐漸形成大衆呼喚真情的“集體無意識”,進而影響創作者的敘事策略與接受者的期待視野。瀆者的審美需求往往受其期待視野的影響,進而決定對作品的選擇,“使得單純‘纏綿悱惻’的風月傳奇,或‘粗豪脫略’的俠義小說,都很難完全令人滿意。‘兒女’與‘英雄’,或日‘‘睛’與‘俠’的結合,可謂勢在必行”。大衆的閱讀需求決定文化市場,制約小說的創作思想與價值取向,進而決定其存在與發展。芸芸衆生在現實中忙於生計,浪漫、真摯的理想愛情往往是一種奢望。張文東指出:“消費文化的主體是日常大衆,但大衆消費的心理需求卻永遠有着超越日常的情感渴望。”武俠小說作者皆以接受對象的審美需求爲創作旨歸,通過對男女俠客愛情的表現與挖掘,將人類愛情悱側纏綿、甜蜜酸楚、色彩紛呈地展現在讀者面前,使其在閱讀中獲得心靈的暫時陶醉。燕青指出:“武俠小說,最引人入勝的情節,尤其是寫男女之間的情感,最使人蕩氣迴腸。”無疑,新派武俠小說的愛情小說敘事,在傳統與現代的融通中暗合了大衆的閱讀情感期待。梁羽生、金庸、古龍:大家以情感敘事構建故事情節,江湖恩怨與兒女情長交織,刻畫出至情至性的英雄豪傑形象。不僅滿足讀者對故事新奇和情節曲折的追求,更契合其尚情心理,使他們在血雨腥風的江湖恩仇中感受蕩氣迴腸的真情,進而產生愉悅的審美體驗。這較之《水滸傳》《三俠五義》《施公案》等倫理化武俠故事的描述,無疑更具吸引力和震撼力,如餘祖坤所云:“成功地使女性情懷、女性之美成了與英雄胸襟、英雄俠義並駕齊驅的一個看點。”實際上,新派武俠小說因此輕而易舉地佔領大衆閱讀市場,獲得的接受效應極爲良好,形成萬衆矚目的空前盛況。
毋庸置疑,以梁羽生、金庸、古龍作品爲代表的新派武俠小說,借鑑言情小說筆法,採用言情敘事構建故事情節,豐富了武俠小說的內涵,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學注重書寫情感的歷史積澱與傳承對大衆期待視野的影響。這對當代武俠小說的創作與研究皆有啓發意義。
轉載請註明出處,謝謝! https://bailushuyuan.org/novel/traditional/reviews/17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