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美國百年外交大敗局》美國外交政策為何總是事與願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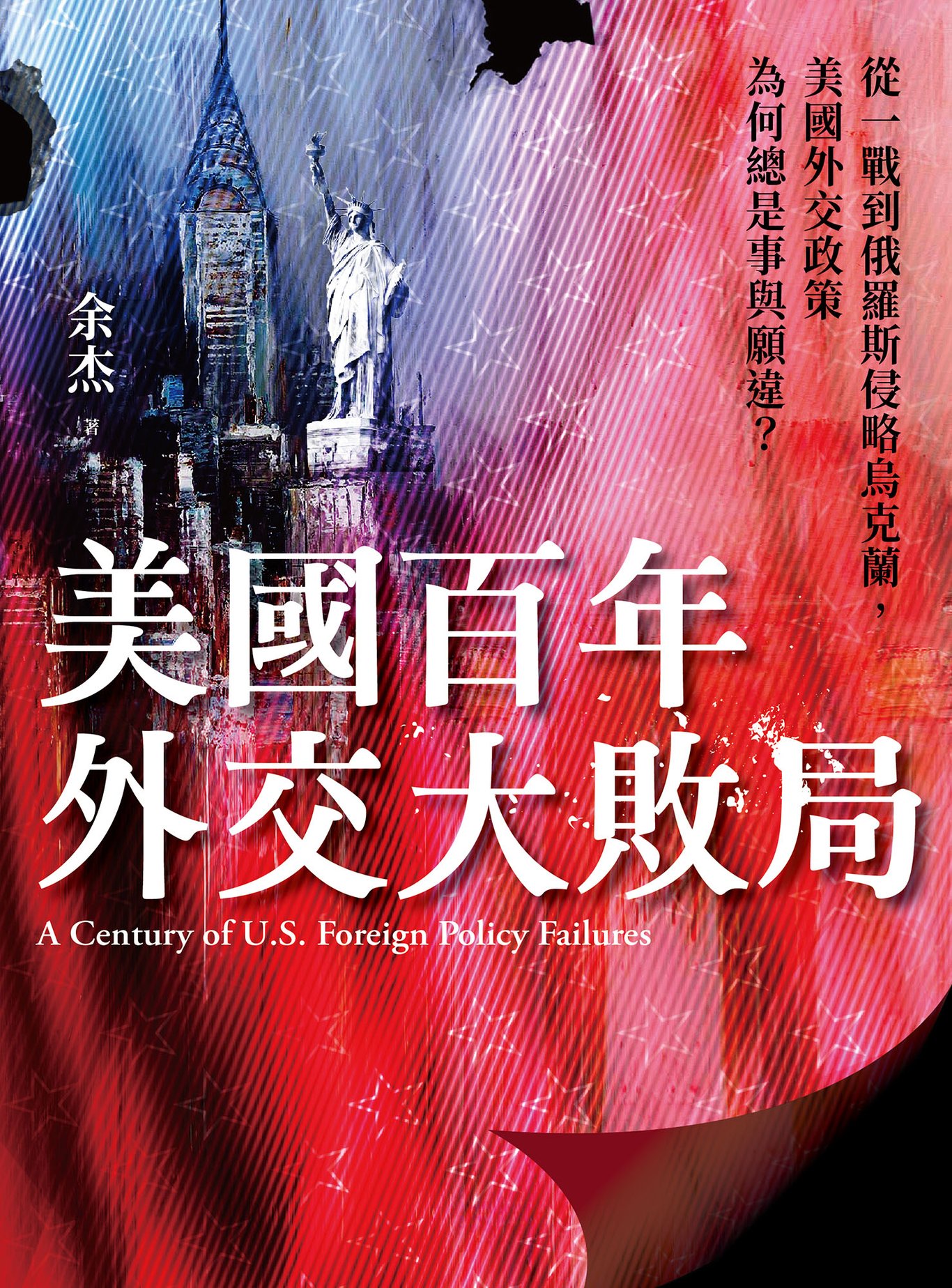
美國外交政策為何總是事與願違?
一九五三年,「冷戰之父」肯楠被排擠出國務院,結束長達二十七年的外交官生涯,退居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剩下的只有「獨處、沉思和寫作」三件事。他曾考慮永遠離開美國,他認為從美國的統治菁英到普通民眾,都狂妄自大、驕奢淫逸,無視國家面臨的深重危機。他不無傷感地寫道:「我想這個國家注定要失敗的,這種失敗一定是悲劇性的,代價巨大的。」
正是在這一人生轉折點上,肯楠開始思考政治、道德和宗教之關係,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相信,上帝不會輕易寬恕我們所做的那些自我貶損、有害尊嚴的事情。」他在從華盛頓開往普林斯頓的列車途中寫道:「這個國家已經激不起我的興趣了。這是一個極其讓人厭煩的國家,雖然它自己絲毫沒有意識到,卻已經注定了悲哀和可憐的命運。」歷史屢屢證明並再次證明,先知在其故鄉是不受歡迎的。
肯楠在二十一世紀之初去世,幸運地看到美國贏得冷戰的勝利(其中有他很大的功勞),卻沒有看到美國很快迎來更重大的危機。
今天,美國面臨著建國兩百五十年以來最嚴峻的內憂外患。外患首先是奉行共產極權主義和天下帝國主義的中國,其次是伊斯蘭恐怖主義,再次是自私自利、以左為旗的「豬隊友」歐盟。內憂則是仇恨美國建國根基的左派勢力——蘇聯共產主義實驗沒有成功讓他們痛心疾首,他們企圖直接在美國內部發起一場無聲的革命,將美國變成第二個蘇聯。
晚近百年來,美國身為占據全球主導地位的超級大國,其外交政策對國際局勢的走向舉足輕重。美國擁有足夠的資源和能力,又站在正義和自由一邊,但美國的外交政策常常荒腔走板、得不償失。美國參與一戰和二戰,付出數十萬子弟兵的生命代價,為何沒有讓世界變得更好,最大的獲利者成了蘇俄?二戰結束後,美國未能避免中國走向赤化,誰應當為丟掉中國負責?韓戰中,美國為何未能取得完勝?美國又是如何身不由己地捲入越戰並留下難以癒合的傷痕?冷戰之後,為何整個伊斯蘭世界高舉反美的旗號?美國幫助中國走向改革開放、擺脫貧困,為何沒有料到重演了「農夫與蛇」的寓言?
美國外交政策的失敗,從技術層面而言,源於民主制度內在的缺陷——擔任總統職位的,有可能是對國際事務一無所知的笨蛋,而總統的任期限制及總統對選民(選票)的依賴關係,使得總統通常忙於能有立竿見影效果的事務,不願耗費過多時間精力制定長遠的外交政策。
長期以來,一個孤僻的菁英群體壟斷了外交和國安領域,並讓此一領域「三權合一」,不受公眾之監督與質疑。他們一次次地留下爛攤子,卻總能全身而退,卸下公職後還能到商界發大財。
今日,人人都在辱罵美國(辱罵美國成為正義的標榜,不用付出任何代價),世界卻比美國建國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美國。
中國、俄國、伊朗三個邪惡國家已結成新的軸心國同盟,而美國的盟友大都陶醉於安樂、喪失了戰鬥精神。美國面對俄烏戰爭、以哈(哈瑪斯)戰爭(正在擴大化為以色列與伊朗兩大近東強權的戰爭)及臺海危機,如何避免顧此失彼、顛倒緩急?如何出手見招拆招、逐個擊破?
這是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國際關係學者羅特科普夫(David Rothkopf)指出,美國政治體系的醜陋和失靈,讓很多有能力提出和回答問題的有識之士對政府職位望而卻步。擁有決策權的人往往不是最聰明睿智的人。美國領導人和美國政府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缺乏長遠眼光,忘記正在應對的是什麼,真正的目標又是什麼」。長遠眼光不是指優良的視力,而是知己知彼、胸有成竹:「長遠眼光需要了解形勢和各種選項,這反過來要求我們了解美國的資源、優先事項以及追求的價值。這不僅僅是對領導人、決策者的要求,在民主國家,這也是對普通民眾的要求。」
羅特科普夫採訪過五十年來的幾乎每一位國家安全顧問,發現美國的外交關係領域不乏技術專家,或許有能力幫助總統解決某一具體的外交難題(即便不能解決,也可以將其暫時掩蓋起來),卻少有將視野放寬在二、三十年之後,乃至更長時間段的、有遠見卓識的戰略家。他由此得出頗為悲觀的結論:「美國國家安全架構不具備戰略思考的能力,不能為未來貢獻有用的思想。……這一結果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美國從冷戰勝利者、世界唯一超級大國一下就走向衰退,並出現一系列引人注目、讓人不安、相互關聯的國際政策失敗、失靈和『啞火』。」
美國並不能自動成為世界領袖,美國必須做出配得上此身分的成就才能贏得盟友的尊敬和信賴,以及敵人的畏懼。外交戰略學者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指出:「美國現在正面臨歷史上真正重要的轉折點,所以它必須做出以前從未做過的事情:為了美國在和平時期的世界領導地位,形成一貫的、在政治上能起支持作用的戰略。」他進而指出,美國應發揮強有力和卓有遠見的領導作用;美國的持續強大和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國家在選擇和追求目標時表現的智慧、勇氣和果斷——「那些嚴謹的美國政策學者以及那些志在領導國家的人面臨的任務,是在歷久不衰的美國政治傳統中找到有效方法,與美國人民的願望和價值取向取得共鳴,贏得他們堅定不移的支持——進而使制定的政策能讓人民在將來某一天為維護它而付出有意義的犧牲。」
但是,他發現,美國政府出現了嚴重的人才匱乏,教育體系和價值判斷漸漸被毒化,「美國最稀罕的事就是找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並且把他在平凡的工作中贏得普通美國人的尊重,視為一個人形成堅強個性和創造有意義的事業所必備的品德基礎」。
從理念和價值層面而言,外交失敗源於內政的混亂,而內政的混亂源於建國原則的動搖。社會學家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承認,今天的美國「被種族或民族對立弄得四分五裂,貧富懸殊不斷擴大,貧困家庭的孩子難以改變命運,即使是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也為不安全感所困」。這些社會現象背後的根源,如貝拉(Robert Bellah)所說,若公民社會、公民宗教和能在政治領域有所發揮的「公民美德」走向衰敗,一個自由民族就無法存續,「一個自由社會解決問題的方式,不僅取決於它的經濟和行政資源,還取決於它的政治想像力」。
美國從來不曾在對外戰爭中傷及肺腑,卻有可能在內部的「文化戰爭」和「心靈失序」中坍塌。在此意義上,美國最大的危機,不是外部敵人的挑戰和威脅,而是民眾的敗壞、道德的淪喪、家庭的解體、信仰的式微。政治哲學家施特勞斯(Leo Strauss)從德國流亡美國之後,離群索居,卻從未停止思考美國的命運。
他的結論是,倘若正義和節制、勇敢和智慧喪失了,共和政體就走到了末日。如今,很多美國人宛如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筆下的「末人」(der letzte Mensch)——末人們自我陶醉,自我滿足,不知驚訝也不知敬畏,不知恐懼也不知羞恥。他們的靈魂退化了,令人厭惡至極。施特勞斯嘲諷說:「是在死人中活著更好呢,還是在一個無聊者的社會中死去更好。」美籍印度裔公共知識分子德.索薩(Dinesh D’Souza)也指出,美國不會被敵人打敗,美國若是走向衰亡,唯一的原因是自殺,實施這項計畫的是歐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 II)及其背後的「深層政府」(Deep State)。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