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的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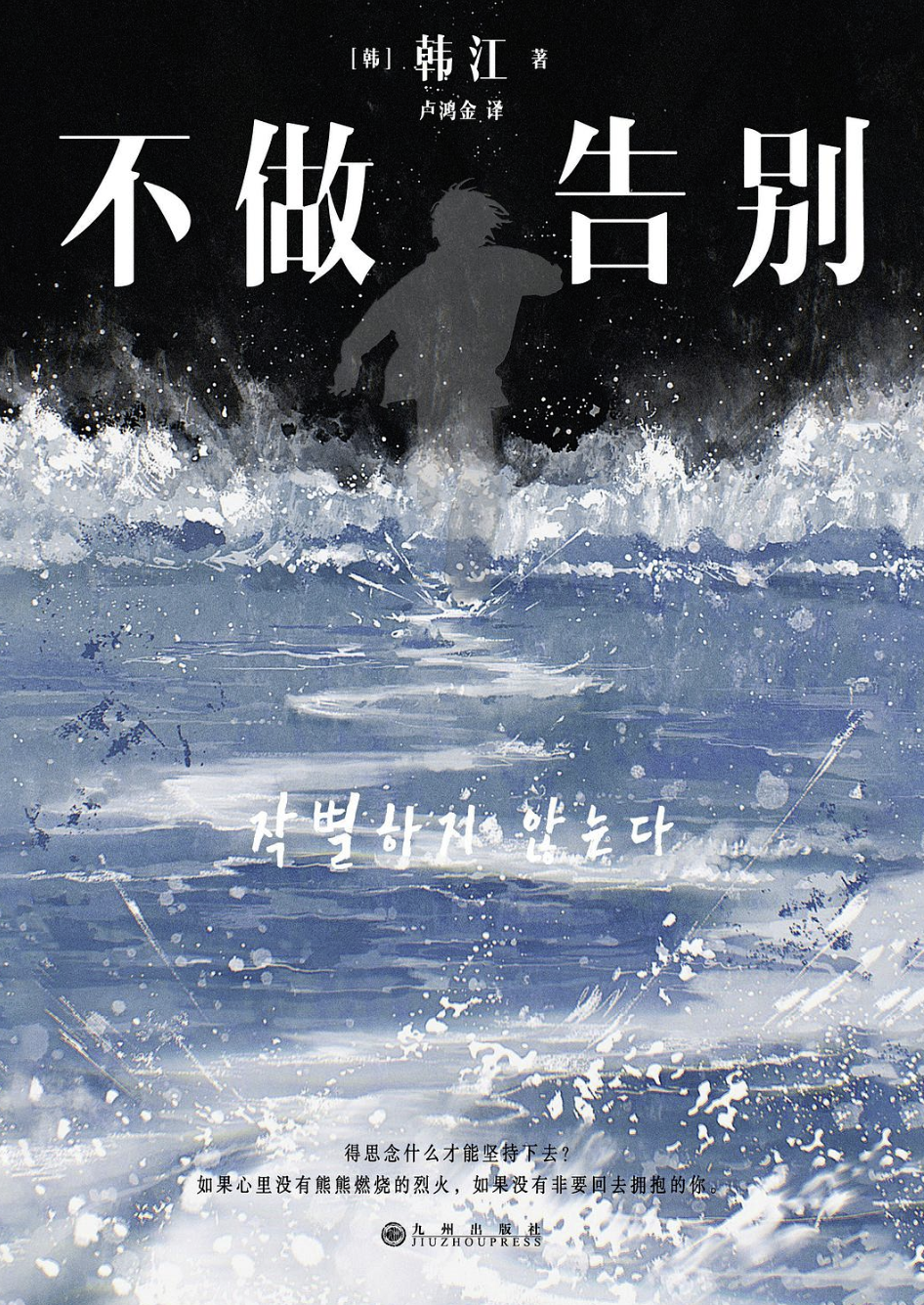
《不做告別》
好迂長和閃回的敘事,在暴雪中的濟州島,在明顯是夢境,或者是瘋了的旅途。如同,我們對於,1950年代發生的任何事,本來就會有的距離感,一種借由,一個又一個碎片,才能看似接近,但根本無法抵達的地方。這就是時間本身,無法逾越,每一個人,都只有屬於他所在時間,的那一種命運。
1960年
「當時有傳聞說贈鏡留下三名幸存者,我認為應該是一人。是個明亮的夜晚。穿著血跡斑斑衣服的青年乞求給他一套衣服換。他快速地飛奔而去。」
「聽到這個事情,媽媽正縮著身體嘔吐著,一直到吐出胃液為止。」
「那個青年並非是舅舅的可能性完全沒有。」
「就像現在坑道裏三千具遺骸中任何東西都有可能是舅舅的一樣。」
.........
與《少年來了》一樣,死亡的是男人,但停留在時間中的,是母親,是妹妹,是女兒。直到她們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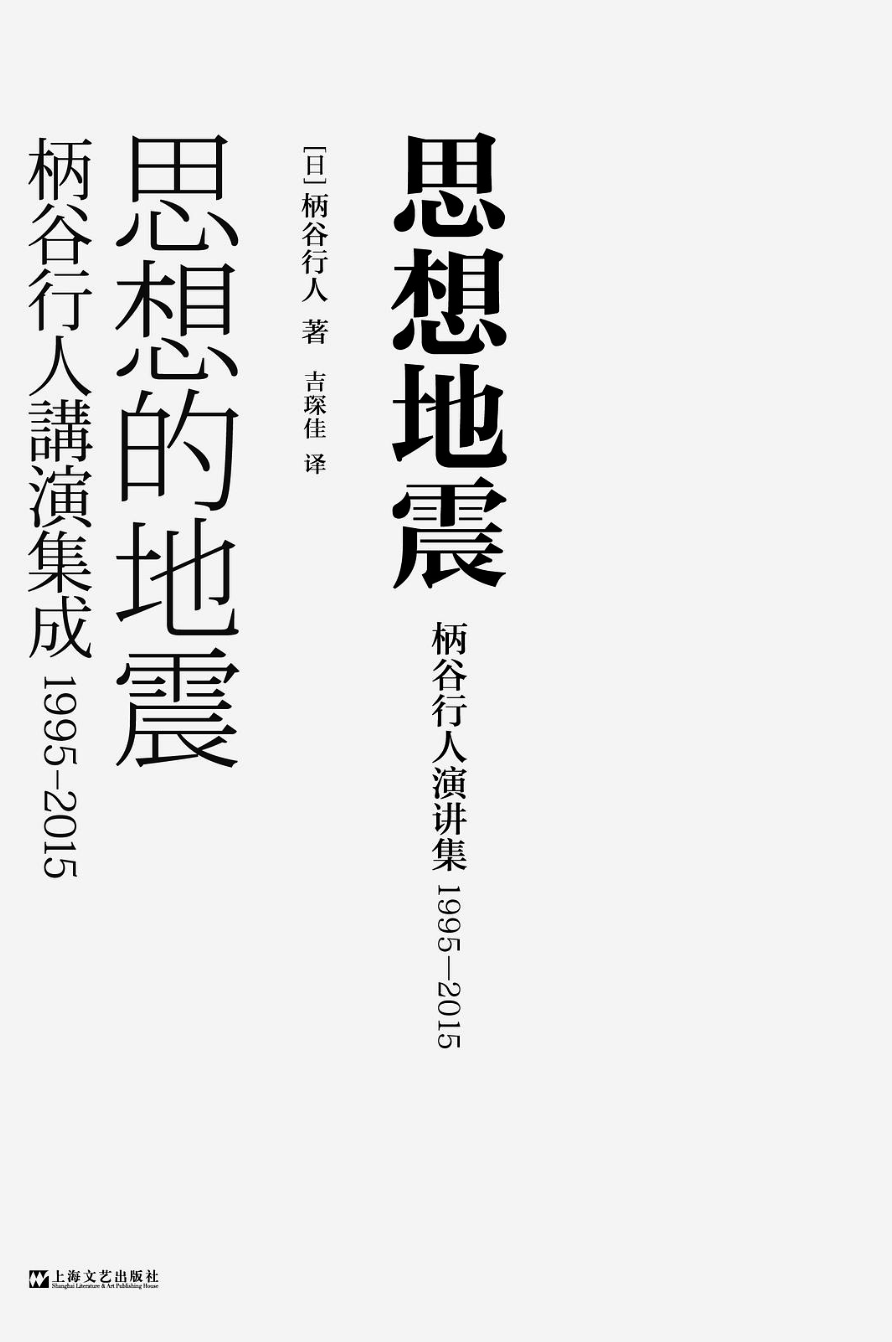
《思想地震:柄谷行人演讲集,1995-2015》
很豐富的一本演講集。1995年,關西大地震、東京地鐵奧姆真理教投毒這本書,讓柄谷行人很震驚。他想到了康德,在1775年裏斯本地震後,行動和思想發生了徹底轉換。很難得的是,書中有一篇關於台灣太陽花學運,不清楚有多少刪節。他指出「議會」(立法院) 和「遊行」、「集會」,在英文中同屬於assembly,借由占領,合二為一了。(幾年前,我也在長沙灣,目睹了類似的情景,但更為短暫。) 這讓他又一次想到蘇格拉底,那個從不參加公民大會,只逗留在廣場、和任何一個攀談的蘇格拉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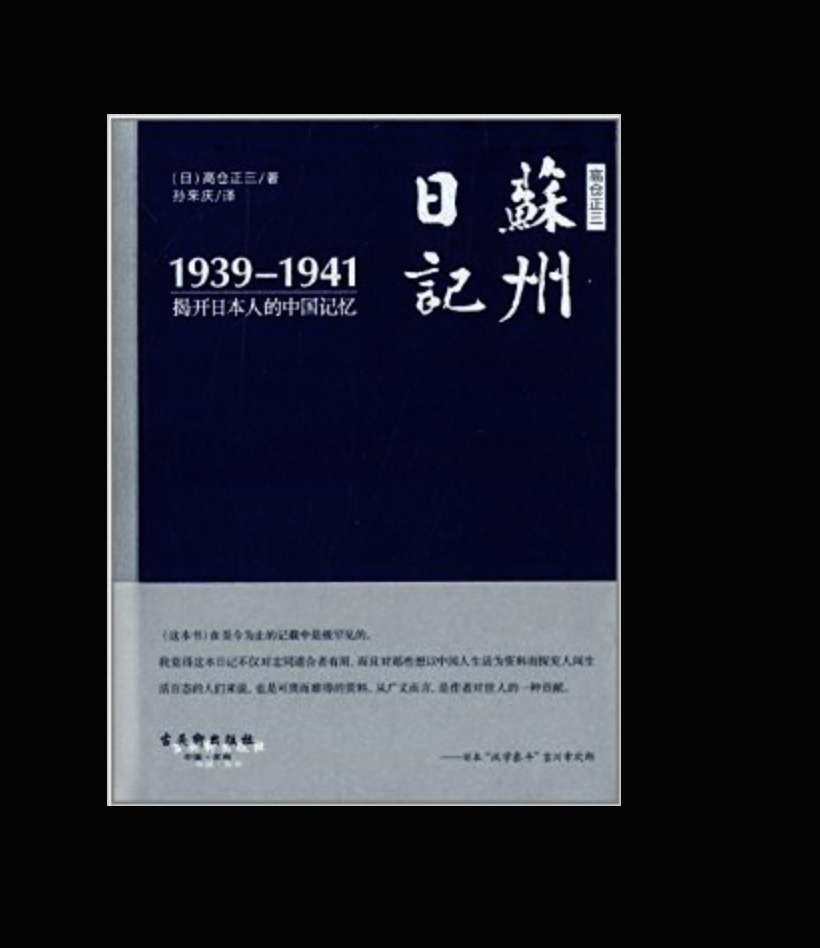
《高仓正三苏州日记(1939-1941)》
挺有意思的。1939年9月,高倉正三來到了蘇州,研究吳地方言、文化。他的日子過得很輕松,日記裏幾乎沒提到戰爭。每天找老師學蘇州話,只要有空就出門玩,去園林、聽評書、逛虎丘、玄妙觀、靈巖山。偶爾,坐火車去上海,四川北路的亞細亞酒店好貴。他期待能在上海住上一陣。因為物價不斷上漲,他也總是沒錢。次年三月,順著長江,在武漢呆了一周,還去了漢川、信陽、嶽陽,返程到了九江、廬山、星子、安慶等地。好景不長,1940年10月20日發燒,之後住進醫院,還在不斷寫日記。次年,3月15年,在蘇州去世,他剛過二十八歲。不久前,他寫給哥哥,最後一封信:「去年的現在,正與佐藤一起邁步於常州和杭州,作長江沿岸的旅行。杭州的優美風景和難以下咽的飯菜至今令我難以忘懷。在只要有人談論起杭州,我便即刻會脫口說出以上的感想。
「蘇州城晚上剛過七時,就連最熱鬧的觀前街行人都很稀少了,護龍街等街上的商店都已全部打烊,四周一片漆黑,去散步也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故鄉無用》
「當然,消失的東西很多,遠不止那些,一點味道也沒留下。小鎮的泳池消失了,圖書舘也消失了。在地圖裏,在那條小河裏,我摸到了媽媽的顫抖。那條紅礫土的路,坑坑洞洞的水坑。整張地圖都消失了,整座家都被鏟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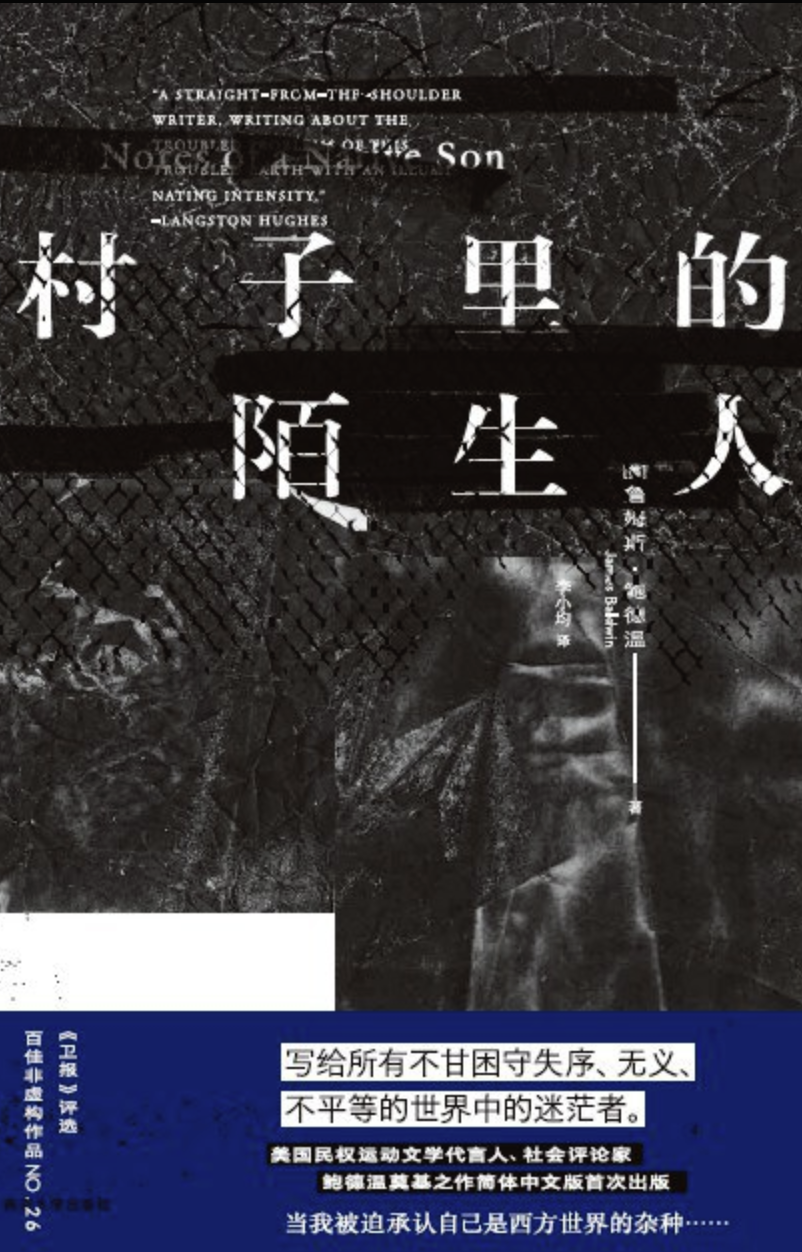
《村子裡的陌生人》
「我們在法庭講完了床單案件的來龍去脈,引起了旁聽席上法國人的大笑。法庭宣判我們無罪。但是,法國人的笑聲令我寒心,哪怕他們是想用笑聲溫暖我們。發出這種笑聲的人,總認為自己安全,遠離所有的不幸;對他們來說,生活的痛苦是假的。我在美國經常聽到這種笑聲,我才決定找一個再不會聽到這種笑聲的地方。在巴黎的第一年,當我深切意識到這種笑聲是普世的笑聲,從來不會消失之時,我的人生,在我自己的眼裏,就以一種深沈、陰郁、冷漠和解放的方式開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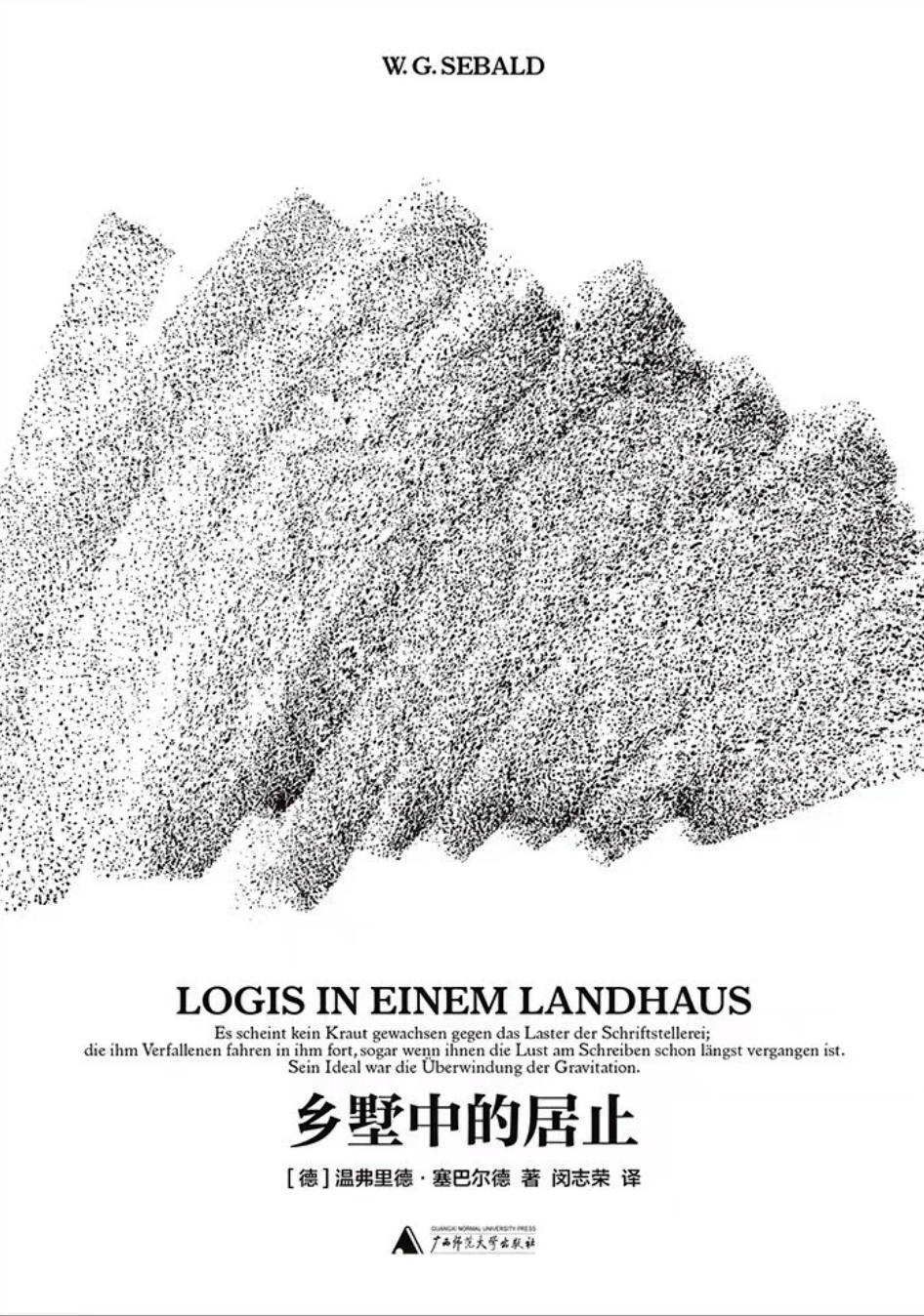
《乡墅中的居止》
「不過瓦爾澤害怕的不是貧窮本身,更確切地說是社會地位下降帶來的恥辱。他非常清楚,人們「會看不起一個身無分文的工人,但是更加看不起一個失業的職員……一個小職員,只要他還有工作,就是半個紳士;一旦脫離崗位,他就會墮落成一個笨拙、多余、讓人討厭、無足輕重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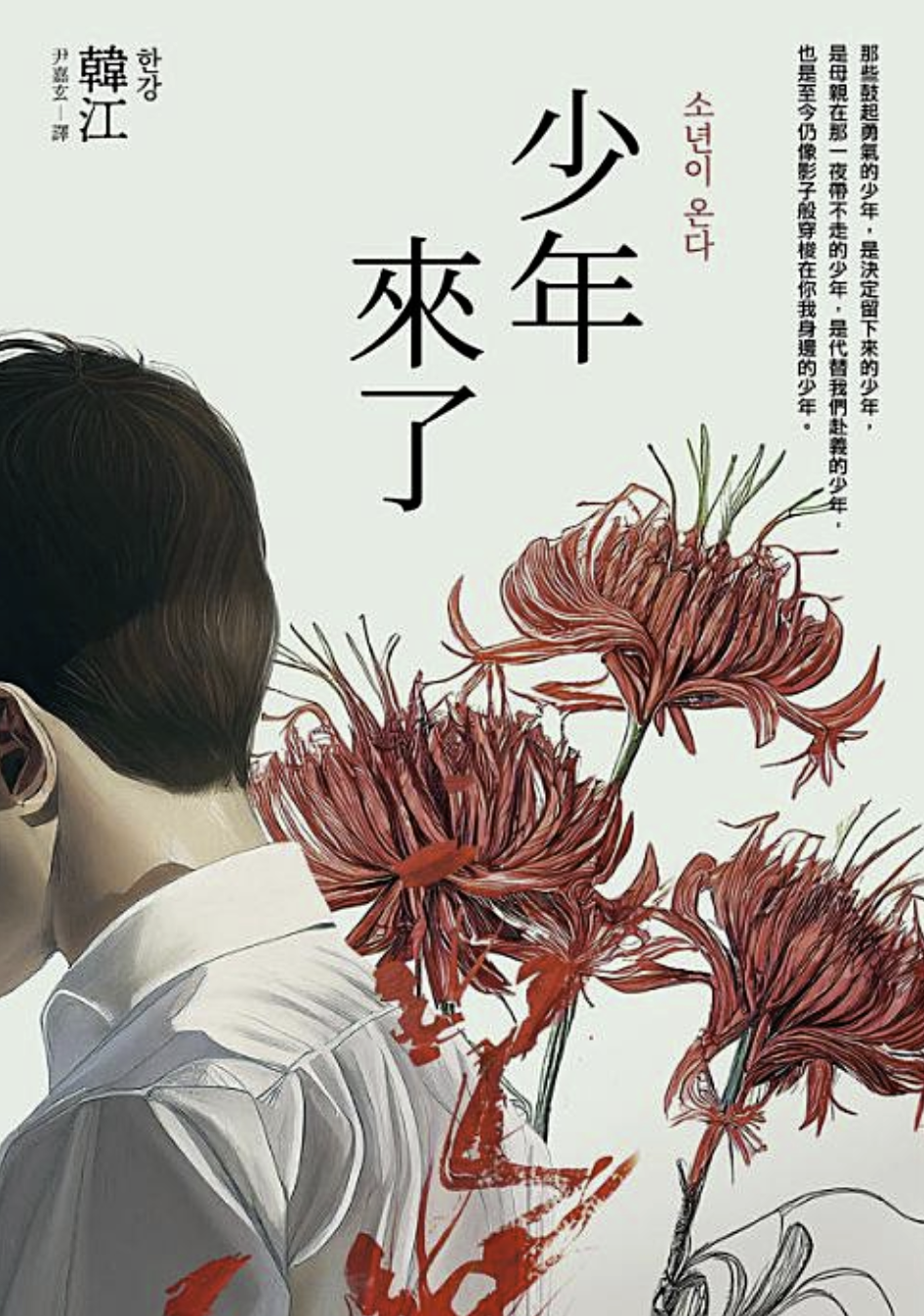
「我奮力拉著幾乎快要情緒崩潰的你向前走,用力高唱著國歌,唱到喉嚨都快沙啞,直到他們在我腰間鑲入一顆像燒燙火球般的子彈,直到那些臉被白色油漆抹去。」
三十年后,他的母亲还是会在街市上,留意着初中生制服,跟着走好久,走好久,以为那是她死于少年的儿子。
END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